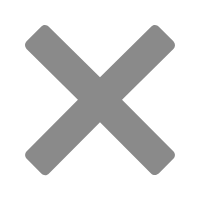-
替身玫瑰的最后一瓣
第3章
可能是喝了很多酒又吃了药的缘故,我睡得格外昏沉,还做了梦。
梦里我回到了大学校园,阳光透过梧桐树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那是十年前的我,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,独自坐在教室最后一排。
周围同学三三两两说笑着,只有我像个透明人,永远缩在属于自己的角落里。
江时蓝就是在那时候闯入我世界的。
她作为班长有职责关心班里每一个同学的身心健康。
见我总是不说话,就反坐到我前方的位置,手肘撑在我的课桌上:
“同学,愿不愿意陪我聊聊天?”
我低着头不敢看她。
那时候的江时蓝在我们系是出了名的风云人物。
家境好,长相出众,成绩永远排在前三。而我来自偏远山区,靠着助学贷款才能来上学。
她歪着头看我,长长的头发从肩头滑下来:
“要一起去图书馆吗?”
我没想到她会这么说,慌乱中碰倒了桌上的水杯。
她敏捷地跳起来,还是被水溅湿了裙角。
我以为她要发火,她却笑了:
“你紧张什么?我又不吃人。”
那是我们第一次对话。
后来她总会有意无意地找我说话——
在食堂“偶遇”时端着餐盘坐到我对面,或是在图书馆“刚好”发现我旁边的空位。
起初我以为她是出于班长的责任感,直到有次我发烧没去上课,她翘了专业课跑来宿舍给我送药。
我哑着嗓子问她:
“你真好,对所有人都这么温柔。”
她正弯腰给我量体温,闻言顿了顿:
“我可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。”
我没敢接话。
她收起体温计,突然伸手揉了揉我发烫的耳朵:
“安景臣,你知不知道你特别容易脸红?”
我们的关系就是从那天开始不一样的。
她不再找借口接近我,而是直接在下课时等我一起走。
周末会拉着我去看画展,虽然我根本看不懂那些抽象派的涂鸦。
深秋的傍晚,我们在操场散步,她把冰凉的手塞进我外套口袋,我僵着身子不敢动,她就笑得前仰后合。
“你怎么这么可爱啊。”
她总是这么说。
大四那年,我们同时收到了A大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。
那天晚上,她拉着我在天台喝啤酒,喝到第三罐时突然凑过来亲了我一下。
“毕业就订婚吧。”
她说这话时眼睛亮晶晶的,像是盛满了星星。
我紧紧攥着易拉罐,铝皮凹陷下去,啤酒泡沫溢出来沾了满手。
那一刻我突然觉得,像我这样的人,原来也配拥有这么好的未来。
研究生三年过得飞快。
江时蓝总笑我像个老父亲,每天提醒她吃早餐,下雨天必定去实验室送伞。
她答辩通过那天,我们约好第二天去民政局领证。
晚上她开车去取订好的戒指,我留在宿舍收拾行李。
电话响起时我正在叠她的围巾。
那头是我一个在医院实习的朋友,告诉我说江时蓝出了车祸。
我宛如晴天霹雳,急匆匆往医院赶。
可他们没让我见最后一面。
待我赶到时,江家已经连夜把遗体运回了老家。
最后我也只是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得知,江时蓝的车祸是刹车失灵导致的。
撞上护栏后,人当场死亡。
我拿着两人的合照在天台顶哭了一夜。
照片上的江时蓝还是笑着的,和那天说要和我订婚时一模一样。
清晨下起小雨,雨水顺着照片滑下来,像极了眼泪。
梦到这里突然变得模糊,我一声呼唤下骤然惊醒。
我盯着天花板,梦里的画面和现实重叠在一起。
两张相似的脸在我脑海中交替浮现,最后定格在江时蓝带着笑的唇畔上。
我吞了两片药,走进卫生间洗漱。
镜子里的男人眼眶通红,嘴角还带着干涸的血迹。
冷水扑在脸上时,我突然想起梦里江时蓝常说的话。
她说:“景臣,你要多笑笑。”
可现在的我,早就忘记怎么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