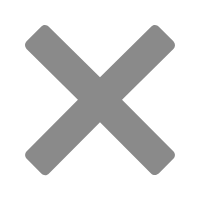-
求了妻子99次看望病重母亲,可她却陪在白月光身边
第2章
我将母亲的骨灰暂时安放在家中,等过几天葬礼的时候再送母亲去安葬。
我抱着沉甸甸的骨灰盒,指尖触到冰凉的瓷面时,恍惚间又看见母亲温暖又慈祥的笑容。
记得我和顾悦可刚结婚的时候,母亲高兴得不得了。
她翻出珍藏多年的相册,拉着顾悦可的手一页页翻看:
“我们家一舟从小就皮,现在可算有人管着他了。”
那些日子,她逢人便夸:
“我们一舟啊,可找了个好老婆。”
“人长得漂亮,工作能力强,性子也好。”
老邻居们打趣她比儿子结婚还高兴,她就抿着嘴笑:
“可不是嘛,这么好的姑娘愿意嫁到我们家,不知道是我和一舟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哦。”
父亲走得早,是母亲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,辛苦把我养大。
为了不让我受委屈,几十年来她都没有组建一个新家庭。
长大后我劝她找个老伴,她总摆摆手:
“妈这辈子啊,就盼着看你成家立业。现在心愿都实现了,还有什么不满足的?”
我摩挲着骨灰盒上的花纹,喉咙发紧。
母亲总是说只要我幸福就好。可最终,我连她最后的愿望都没守住。
对不起母亲,还是要让您失望了。
我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,哭着昏睡过去。
不知过了多久,一杯刺骨的冰水突然泼在脸上,我猛地惊醒。
顾悦可站在床边,手里拿着空杯子,居高临下地睨着我:
“睡够了?现在给我解释清楚,电话里那些话是什么意思?”
我抹了把脸上的水珠,刚睡醒嗓子还有些沙哑:
“你想听什么解释?”
“谁准你提离婚的?”她一把掀开我身上的毛毯,尖锐的指甲戳在我胸口,“江一舟,你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!”
“要工作没有工作,要样貌没有样貌,一个大男人成天窝在家里捣鼓什么锅碗瓢盆,全靠我养着你!”
“你个废物!离了我,你连饭都吃不起!”
她大概忘了,从前的她是怎样挽着我的胳膊,求我待在家里做饭给她吃。
她曾说过最喜欢吃我做的饭,可如今我就算做出一桌满汉全席也比不过景子澈给她煮一碗泡面。
我沉默地起身,从抽屉里取出下午律师刚拟好的离婚协议。
“说够了吗?说够了就签字。”
“你——”她夺过协议书,却在看到财产分割条款时瞳孔骤缩,“你要分走一半?江一舟你配吗?”
我冷冷地盯着顾悦可:
“你想清楚,这已经是看在往日情分上让步了。当年公司是怎么起家的,我又为什么退出公司,需要我提醒你吗?”
她的表情突然僵硬,那些被刻意遗忘的记忆重新浮现出来。
说实话,我要分走顾悦可一半的财产还有公司里20%的股份,这个数字,远远不及当年我对公司付诸的心血。
七年前,我和顾悦可挤在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创办了现在这家公司。她负责幕后,我则没日没夜地在外奔波跑业务。
我陪投资人喝酒喝到胃出血,为赶项目连续熬通宵,最困难时甚至卖了父亲留给我的表。
后来公司上市,她在庆功宴上举着香槟对我说:
“一舟,我不想当依附丈夫的家庭主妇。”我当即点头:
“你想继续工作,我支持。”
但她搂着我撒娇,说舍不得看我辛苦奔波,让我留在家里享福,她养我。
后来母亲患病,我不得不将重心转移到家庭上。
渐渐地,我的名字从公司管理层中消失了,连公司的门禁我都刷不进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