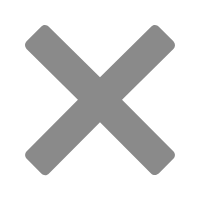-
撞见丈夫和情人在卧室厮混,我死了心离开他
第2章
半个小时后,像是故意对我示威一样,宋临川发来的照片里,她和白昭昭泡在满是泡沫的浴缸里,两手十指交扣,他的无名指上还留着婚戒摘下的淡淡痕迹。
我盯着手机屏幕,意外地发现自己竟毫无波澜,甚至还有点想笑。
毕竟,这早已不是宋临川的第一次出轨。
两年前,宋临川第一次出轨被我撞见。
我整个人浑身都在发抖,牙齿都在打颤,只挤出两个字:
“离婚。”
那时的我,爱得纯粹而又偏执,容不得半点背叛。
即便他跪在我脚边哭到天亮,即便他一遍遍解释那只是个意外。
我哭了一整晚,却始终没有松口。
后来那一个月,宋临川每天变着法子求原谅。
他带我去我们第一次约会的餐厅,翻出大学时的照片,把我们从相识到结婚的点点滴滴翻来覆去地讲,甚至在我公司楼下等一整天。
看着他憔悴的样子,我终究心软了。
那段时间他确实做得很好。
给我写保证书,事无巨细地报备行程,推掉应酬回家吃饭。
可惜好景不长,不到半年,我又撞见他出轨公司里的实习生。
宋临川当时辩解说是喝醉了,错把对方当成了我。
我什么也没说,只是冷笑着看他,直到他恼羞成怒地摔门离去。
自那以后,宋临川的出轨变得肆无忌惮。
他不再遮掩,连借口都懒得编造。
他开始光明正大地带着情人招摇过市,领到家里胡来的次数更是数不清。
我开始陷入漫长的自我怀疑。
每天清晨对着镜子时,都会不自觉地审视自己日渐憔悴的面容。
眼角的细纹、有些松弛的皮肤。
是不是我真的已经毫无魅力了?
是不是我太过乏味,才会让宋临川一次次向外寻求刺激?
这种念头像毒蛇般啃噬着我的神经。
我开始整夜失眠,大把大把的头发落在枕头上,洗手池里。
心理医生诊断书上的“重度抑郁”四个字刺得我眼睛生疼。
我就像被困在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,每次以为找到出路,转角又会撞见宋临川和另一个陌生女人纠缠的画面。
那些记忆碎片不断在脑海中闪回,让我在凌晨三点的卧室里窒息到想要尖叫。
最可怕的是,我明明清楚地知道这段婚姻已经病入膏肓,却像被施了咒语般,始终无法挣脱这个令人作呕的牢笼。
每次下定决心要离开,宋临川轻描淡写的一句“老婆,我今晚回家吃饭”又让我可悲地重燃希望。
我跟他吵过,闹过,最严重的那一次,甚至动了刀子。
我抄起水果刀抵在他脖子上,声音嘶哑:
“宋临川,既然你管不住自己,做不到一心一意,那就离婚,你图个痛快,我也好解脱。”
我知道我病了,我被宋临川逼得疯到不像我自己。
可他只是疲惫地叹了口气,伸手轻轻推开刀刃:
“清音,你不要闹了,闹大了对你有什么好处?”
“我向你保证,宋太太永远是你,能名正言顺地站在我身边的人,也只有你一个。”
更可笑的是,连我们身边的朋友也都来劝我:
“临川这么能赚钱,你就知足吧。钱一分不少拿回家,心里也惦记着你,还有什么不满意的?”
“他在外面玩归玩,心里最重要的还是你。女人要大度点,何必闹得这么难看?”
“外面那些不过逢场作戏,多少个也越不过你,非要跟临川闹,不是自找没趣吗?都多大人了,就别追求爱不爱那一套了。”
这些话像钝刀割肉,让我在屈辱中渐渐麻木。
我花了很长时间,才肯承认,宋临川不再爱我了这个事实。
我终于明白,记忆里那个牵我手会耳尖泛红的少年,那个在婚礼上紧握我的手,泣不成声地说“这辈子只爱沈清音一个”的丈夫,我深爱的那个宋临川,早就死在了他第一次出轨的那个夜里。
现在的宋临川,只是个顶着相同皮囊的陌生人。
第二天一早,我给昔日的恩师陈教授打了个电话。
“老师,你的科考队还需要人手吗?我想参加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当年毕业时,陈教授就极力邀请我加入她的科考项目,那是国内顶尖的研究团队,但需要常年驻扎在环境恶劣的野外基地。
但宋临床抱着我说:
“清音,我舍不得你去那么远的地方。”他晃着我的手臂撒娇,“你就待在家里,我养你就好了啊。”
“清音,”陈教授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,“你考虑清楚了吗?加入团队条件艰苦不说,期间可能几个月都联系不上外界。”
她顿了顿:
“临川他......同意你去吗?”
“老师,”我打断她,语气坚定,“我已经决定离婚了。”
“怎么会这样,你们吵架了?”
我笑着点头,想了想又摇头:
“是宋临川出轨了。”
“你们十年的感情,你真的能放下?”
“没什么放不下的。”我抹了把脸,“老师,我需要离开这里,越远越好。”
“好!清音,你来,你的位置,老师一直留着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