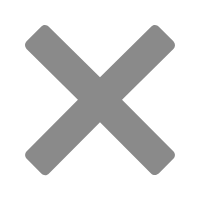-
重生后我不再为她赴汤蹈火
第3章
我原以为那天以后,沈初韵会极早地选择韩溪。
可她竟然选择了报复我,甚至报复方式还来得幼稚又可笑。
不是在我们训练场周围晃悠,就是守在我们营区门口。
可我全都置之不理,连她开学前说要见我最后一面我都拒绝了。
日子平平稳稳过着,转眼就又是一年。
八月的北京像个蒸笼。
我正在操场带新兵训练,通讯员急匆匆跑来:
“万营长!电话!说是沈同志急性肠胃炎送医院了!”
我眉头微蹙:“肠胃炎?她在哪家医院?”
“军区总院!电话那头说疼得直打滚,一直在喊您名字……”
听到这,我原本就有的猜疑顿时确定下来几分。
沈初韵的肠胃不好,从前我向来管着她不准她吃太多生冷的东西。
她自己也知道注意。
怎么会偏偏就赶在这时候生了病,还不找父母直接把电话发到我这里?
怀疑归怀疑,我还是拎着衣服出发去了医院。
一推开病房门,消毒水味扑面而来,沈初韵脸色苍白地靠在床头。
只是不想韩溪也在,正拿着勺子喂她喝粥。
看到我进来,沈初韵眼睛一亮,随即故意往韩溪身边靠了靠。
“韩溪,我疼……”
她虚弱地唤了两声,手指悄悄拽住了韩溪的衣角。
我视若无睹,只是把拎来的麦乳精和罐头放在床头柜上:
“听说你病了。”
“医生说吃了太多冰的。”韩溪接过话头,语气里带着责备,“一口气吃了三根冰棍,还半个西瓜……”
沈初韵突然咳嗽起来,韩溪连忙给她拍背。
她趁机靠进他怀里,眼睛却一直偷瞄我的反应。
此时此刻,我原先的猜想算是彻底得到了确定。
于是我也没心思跟她两人周旋,
转身就往门外走:
“东西送到,我走了。”
“等……等一下!万承勋!”
身后传来“咚”的一声响,沈初韵竟然光着脚跳下床追了出来。
她在走廊上拽住我的袖子,声音发抖:
“你就这么走了?”
我甩开她的手:
“不然呢?看你表演郎情妾意?”
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赤裸的双足,脚趾蜷缩着,眼泪噼里啪啦掉:
“万承勋……你明明最怕我生病的。”
“以前我咳嗽一声你都要紧张半天,现在我都住院了,你就这个态度?”
我这才仔细看她——
瘦了一圈,手腕细得能看见骨头,病号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。
从前我精心调养出来的好气色,如今只剩下一片憔悴。
我冷笑:“沈初韵,用自残来要挟别人,幼稚不幼稚?”
她像被扇了一耳光似的僵在原地。
“我……我只是想见你……承勋,我们谈谈吧,好不好?”
“谈什么?”
“跟我去厦门吧!”她突然抓住我的手,指尖冰凉,“就像我们原来计划的那样,你陪我去南方,我们重新开始……”
“现在正赶上改革开放,你用你的人脉和见识为我保驾护航,我相信我们会闯出自己一片天地的!”
我差点笑出声来。
上一世我就是听了这句话,放弃大好前程跟她南下,结果成了她口中“束缚她自由的枷锁”。
于是这一次,我没再给她好脸色。
我一把拽过她,直接推进跟出来的韩溪怀里:
“沈初韵,你看清楚,这才是你自己选的港湾。”
韩溪手忙脚乱地接住她,脸上闪过一丝得逞的笑意。
可沈初韵却像碰到烙铁似的挣开他,又要扑过来拉我。
“承勋!你别把我推给别人,我知道错了!我以后再也不跟韩溪……”
“晚了。”我后退一步,“从你说喜欢我,可心里允许另一个人靠近你的那一刻起,我们就彻底完了。”
她呆立在走廊中央,泪水大颗大颗往下掉。
护士推着药车经过,奇怪地看了我们一眼。
“你以前……从来不会这样对我的……”
“是啊,”我整了整军装领口,“所以活该我被你们联手送进太平间。”
这句话说得很轻,却像一记重锤砸在她心上。
沈初韵茫然地睁大眼睛:“什么太平间?”
我没回答,转身走向步行梯。
身后传来沈初韵歇斯底里的喊声:
“万承勋!你给我说清楚!”
下楼前,最后映入眼帘的是她瘫坐在地上的身影。
和韩溪假惺惺去扶她时,那只悄悄摸上她腰际的手。
走出医院大门,热浪扑面而来。
我摸出根烟点上,深深吸了一口。
重活一世才明白,有些人,你把她捧在手心,她嫌你束缚太多。
你放她自由,她又怪你不够在乎。
所以,这种人的心是捂不热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