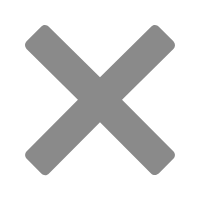-
和女富豪联姻后,前未婚妻悔疯了
第2章
“承烨!”
我转头,看见沈唯一从咖啡厅门口跑过来,身上还穿着昨天抢婚时那条白裙子。
“你怎么在这儿?”
“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。”
我冰冷的态度让沈唯一的脸上闪过一丝错愕。
她愣了愣,随即又摆出一副笑脸想来拉我的手,却被我侧身躲开。
“有事?”
沈唯一的手僵在半空,脸上露出委屈的神色:
“承烨,你还在生我气吗?是我对不住你,可我也是没办法……”
“阿哲他要娶的那个女人名声那么差,我不能看着他往火坑里跳!”
“你能理解我,也是支持我的,对不对?”
我心下冷笑,她给她的竹马思考这个,顾虑那个。
结果让我成为全北城的笑柄,还想让我体谅理解她?
真是做春秋大梦。
我扯扯嘴角:“不好意思,不理解也不支持。没什么事我先走了。”
我错过她的肩准备离开,却被她突然叫住:
“承烨!我……”
“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,但我和阿哲是真心相爱的,你能不能体谅我一下?”
她往前凑了凑,声音又像从前的每次撒样示好一样放软:
“我只是不能给你名分,但我心里是有你的……我们依然可以保持恋人的关系。”
“现在不是很多有钱人都这样吗?司空见惯的事,你别太较真了啊。”
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她毁了婚约,抢了别人的联姻对象,现在居然想让我当她的“地下情人”?
甚至让我别太较真?!
我一瞬间一种反胃感涌上心头,蹙眉看向她:
“沈唯一,你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。”
“我们之间,从你昨天抢婚那一刻起就已经结束了。大家以后井水不犯河水,还能相安无事。”
“结束?”沈唯一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,“宋承烨,你别给脸不要脸!”
“我肯回来找你,是给你面子!你以为离开我,还能找到更好的?”
“能不能找到,就不劳你操心了。就算再找不到,也比找一个想脚踏两条船的好。”
说完,我绕过她,头也不回地走出咖啡厅。
身后传来沈唯一气急败坏的跺脚声,但我懒得再理会。
车子快开到家门口,我这才想起户口本还在老宅存着。
干脆方向盘一转调了方向,正好回去把结婚的事跟我爸妈说声。
我本想速战速决,却没想我刚把时安澜的名字带出来,父亲的脸瞬间阴云密布。
“宋承烨,你被沈唯一悔婚这事还没掰扯清楚,现在又要跟时家那个上不得台面的女人结婚?你是嫌咱们家不够丢人是不是!”
我把公文包放在沙发上,语气尽量平和:
“这是两码事。沈唯一毁约在先,时家的提议于我们而言——”
“于我们而言?”母亲突然插话,嘴里念念叨叨的,都是时家今时今日的地位。
“老宋你懂什么?时家在北城什么地位什么身份你没数?”
“时安澜就算名声再不好,背后的人脉资源是实打实的!承烨跟她结婚,对公司拓展南方市场有百利无一害。”
父亲冷笑一声:“人脉?你也不看看外面怎么说她的!”
“说她是交际花,说她换男人比换衣服还勤!我们宋家的儿媳,怎么能是这种名声?”
“名声能当饭吃吗?”母亲走到我身边,拍了拍我的肩膀,“承烨做得对,婚姻就是利益交换,感情能值几个钱?你看沈唯一,跟你谈了那么多年的感情,还不是说跑就跑?”
他们你一言我一语,父亲骂我糊涂,母亲算着利弊。
却没一个人问过我“时安澜这个人实际怎么样”,更没人提过“你是不是真的愿意”。
我盯着茶几上那盆开得正盛的文竹,突然想起小时候第一次拿到奥数冠军。
父亲夸我“给宋家争了光”,母亲说“以后能换更好的资源”。
后来我想选艺术系,却被他们联手压下,理由是“学那个没出息,得给家族生意铺路”。
原来从始至终,他们教我的只有两件事:利益和家族。
“自我”这个词,在他们的教育里像团被揉碎的废纸,早被扔到了角落里。
这顿饭吃得相当沉默。
当然,只有我自己沉默。
我最终还是把户口本带走了。
离开老宅时,我坐在车里,看着后视镜里越来越小的家门,突然觉得有些恍惚。
这栋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,竟像个精致的牢笼,每根栏杆都刻着“家族利益”。
突然手机叮咚一声响,是时安澜发来的消息:
“在干嘛?”
我想了想,还有闲心跟她开起玩笑:
“在披荆斩棘。”
她竟然马上理解了我的意思:
“家里人很反对吧?”
是在疑问,可语气中又充满了笃定。
我还没来得及打字,又一条消息跟了进来:
“来城南别墅吧,带你看看房子装潢。你要是不喜欢,现在改还来得及。”
我犹豫一瞬,想着换换心情也不错,于是回了个“好”便驱车前往。
车子停在别墅门口,我刚把钥匙插进锁孔,门缝里就飘出一阵钢琴声。
我推开门,玄关的感应灯应声亮起。
而那琴声还在继续,从客厅的方向流淌出来,裹着室内淡淡的香薰味,莫名让人心头一松。
我轻手轻脚探过头,看到的竟是时安澜坐在琴凳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