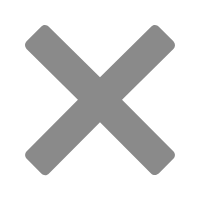-
美人皮
第三章
醒过来时,我还在西厢,却盘坐在家中的米缸里。
我家中富裕,从不吃糙米,缸里都是褪了三遍壳的白米。
我身子被米紧紧裹着,只露出半个肩膀和一个头。
爹娘坐在我身边的小板凳上。
我娘眼底乌青,眉毛鼻子都有些寡淡,仿似没怎么睡好。
她抚了抚我的脸蛋。
“娴姐儿,九天玄女的皮影裂了,让娘剥了你的皮,做一个新的好不好?”
我哇地一声哭出来,“娘,别剥我的皮,娘我听话,我去嫁人,嫁了人就能换皮影回来了不是吗?”
我娘先是嗤笑,继而眼里又染上几分哀伤。
“娴姐儿,嫁人那话是娘骗你的,娘也舍不得剥你的皮,娘是没办法……”
娘这话我信。
三个姐妹里,我长得最像我娘,不止样貌像,连皮子也像。
我全身上下无一根汗毛一个斑点,白得透亮。
爹常说,我和我娘一样,有张美人皮。
我娘哭着打了个嗝,“娴姐儿,不剥你的皮,你爹的神仙戏就没法演了啊!”
“娘,我爹一场戏就是五两金,这戏我爹已经唱了十八年,咱们家的钱够多了,就是到了京城都能买宅子活几辈子,娘你求求爹,这钱不挣了好不好。”
我娘欲言又止。
见我始终不松口,她泪眼汪汪地看了看我爹。
“加水。”
我爹听了,转身拿起水瓢,舀了缸里的水,浇在白米上。
没多会儿,吸了水的米一点点膨胀,我喘不上气来了。
娘哄着我,“娴姐儿,做皮影有个讲究,非得美人皮自己同意了才行,你就松口吧,不然多遭罪。”
我摇头。
爹便继续往米里加水。
渐渐的,我撑不住了。
只想赶紧从缸里脱离出来,好大口大口喘气。
“娘……”我气若游丝,“我答应你。”
这话刚说完,我娘一直寡淡的眉眼突然鲜活起来。
我爹将我从米缸里捞了出来。
娘则笑着跟我说,“娴姐儿听话,娘剥皮的时候一定小心,不让姐儿疼,好不好?”
可我哪还有力气答话。
堪堪把气儿喘明白了,我娘说要给我梳梳头。
只两三下,她便将我头发用麻绳束好了。
而后又绑上更粗些的绳子,直接薅着头发,将我吊在了房梁上。
头皮被生生扯着,我哼唧着喊疼。
我娘让我忍一忍,而后封住我的嘴。
她剥了我的衣裳,只留一个肚兜。
肚兜细细的带子堪堪挂在颈间,娘怕我着凉,给屋里升了个炭盆。
炭火劈啪作响,娘扒拉了两下。
将我扔下便出了门。
没多久,我听见她喊我爹。
说翻了黄历牌,今天日子好。
那两人又没羞没臊开了。
而我被折腾一遭也累得够呛,竟这么睡过去了。
再睁眼就又到了夜里。
我娘在烧好的水里加了花汁子,一下一下,用她还在滴血的手给我洗身子。
洗好了,又拿香膏里里外外给我涂了个遍。
娘说,这次要做的是九天玄女,可得仔细着点养我这身美人皮。
因为我爹那神仙戏灵不灵,全指着九天玄女。
全都忙活完了,娘给我穿上肚兜,拖了箱子过来。
她拿出里面的皮影,一张张铺在窗棂上晒月光。
再拿起笔,将那些眉眼淡掉的,颜色不水灵的,重新描了描。
一直到拿起了九彩石和八卦镜。
我娘半眯着眼看了半天,挑了眉尾问我。
“你还没告诉娘,昨儿夜里,怎么突然就到西厢来了?”
我不出声。
娘站起身,伸手碰了碰我的脚尖。
我低头去看。
我娘那张脸极美,又生得嫩,一脸的俏皮,瞅着竟比我没大几岁似的。
我忽地倒吸一口凉气。
我才发现,打我出生后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娘的脸竟然一点都没变!
娘见我神情有异,笑容冷了下来。
“娴姐儿,你昨晚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,所以才来了西厢?”
我摇头。
娘扁扁嘴,将皮影收进箱子里锁好,放到了窗根下。
可阿娘前脚才走,我的泪就落了下来。
我娘说得没错,我是想起些东西来。
我想起两个姐姐已经死了。
我目睹过,但不知我爹娘用了什么法子,让我给忘了。
昨夜我在西厢晕倒后,就都想起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