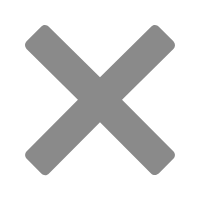-
小姨卖掉祖传医书供我上学,二十年后我回村报恩
第2章
去镇上的路有二十里,我穿着打补丁的布鞋,走一步捏紧一次借条。
站在大姨家红砖墙外,铁门上的铜环已经被日头晒得发烫。
我刚抬手敲门,门就“吱呀”开了道缝。
大姨系着碎花围裙探出头,看见我时眼皮子猛地一跳:
“望娃?你咋来了?”
她话音没落,眼神就跟探照灯似的在我身上扫了一圈,最后定在我露着脚趾头的补丁布鞋上。
我下意识把脚往后缩,大姨见状干笑两声:
“快,快进来,这天儿热坏了吧?”
她侧过身让我进门。
我跟在她身后,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到处张望。
屋里亮堂得晃眼,奶黄色的墙纸贴着风景画。
沙发罩子雪白雪白,比我家土炕头的油布干净十倍。
我踩在水泥地上不敢挪步,生怕鞋底的泥点子蹭脏了地板。
大姨指了指沙发:“坐呀,我去倒水。”
“诶,好!”
刚坐下,里屋就传来“哐当”一声响,是大姨儿子小宝的嗓门:
“妈!我又没鞋了!你看看这些,都去年的款了!”
“我同学他们都穿‘回力’,你给我也买双呗?”
我闻言看了看自己初中后就没换过的破布鞋,下意识把脚往后藏了藏。
正往沙发缝里缩脚呢,就听见大姨在里屋哄他:
“不喜欢就买新的,明儿妈带你去供销社,一百多块钱的事儿,咱不差这钱。”
她顿了顿,又说:
“对了,你二姨家望娃来了,出去打个招呼。”
小宝“哼”了一声:“我才不出去,穷亲戚有啥好见的。”
穷亲戚三个字瞬间重重烙在我心里。
我抿着唇,盼着大姨能说点什么,救救我可怜的尊严。
可大姨没再吭声,踩着拖鞋出来了。
她把杯子往茶几上一放,玻璃台面映出我拘谨的脸:
“望娃今儿咋有空来玩?”
我抠着裤腿上的补丁,嗓子眼发紧。
犹豫半晌,还是挑了个没那么突兀的切入点:
“大姨,我……我考上大学了。”
“考上大学好啊!”她眼睛一亮,“哪个大学?”
“北京大学。”
“哎哟!那可是名牌!”
大姨拍着大腿,可笑容还没挂稳,就听见我小声说:
“大姨,我这次来……是想请您帮个忙。”
我的声音细弱蚊蝇,大姨一听脸色稍稍一变,打量我一眼:
“帮什么,你说吧?”
“我……我想跟您借一部分学费。”
空气突然凝滞了,沉默的气氛压得我快喘不过气。
我生怕她觉得我是来要钱,赶紧把借条递过去:
“我,我写了借条,等我毕业工作了一定还,按月还按周还都行……”
“大姨,上大学是我的梦想,也是我爹娘的遗愿,您……”
我话还没说完,大姨的脸色已经沉了下来,接过借条瞟了两眼就放在桌上:
“哎呀,望娃,不是大姨不帮你……”
“只是你姨夫前阵子进货赔了本,眼下人还在外地催账呢,家里就剩我跟小宝孤儿寡母,开销大着哩!”
“我可以分期还的!”我往前凑了凑,“或者把我家那头猪抵押给您,还有老宅……”
“诶哟你这孩子咋听不懂话!”
大姨突然提高了嗓门,借条一甩扔回我脚边:
“我说了没钱!我家穷得都揭不开锅了,哪有闲钱管你什么狗屁梦想!”
她猛地站起来,从裤兜里掏出个手绢包,抖落出五张十块的票子摔在桌上:
“这五十块你拿着,多了没有!”
“能给你的就这些,别让邻居看见说我苛待外甥!”
手边的票子上还带着大姨的体温。
可我盯着那五十块钱,脑子里全是刚才她在里屋说的“一百多块钱的事儿”。
小宝一双鞋够我交小半个学期的学费,可她打发我时,连个鞋前都不够。
“大姨……”
“别叫我了!”她打断我,脸上全是不耐烦,“你说你能还?拿什么还?别到时候拿我家钱去打水漂!”
“行了行了,快走吧,别在这儿耽误我做饭。”
她催着我离开,在我走后,铁门“砰”地一声迫不及待关上。
我攥着那五十块钱站在巷口,日头晒得人发晕。
我把借条塞进裤兜,回去的脚步却像灌了铅。
路过供销社时,看见橱窗里摆着“回力”球鞋,标价签上的“128元”刺得我眼睛疼。